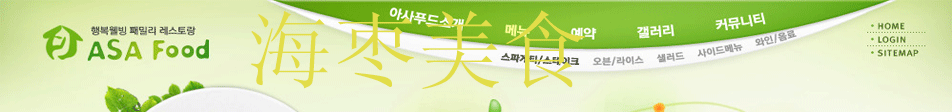|
有白癜风怎么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6%9D%A5%E4%BA%86%C2%B7%E5%B8%A6%E4%BD%A0%E8%B5%B0%E5%87%BA%E7%99%BD%E7%99%9C%E9%A3%8E%E9%98%B4%E9%9C%BE/20783753?fr=aladdin 泰山,即使没有去过的人,也非常熟悉它。“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关于泰山的赞美之词不计其数。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一座人文之山。它是当仁不让的五岳之首,是历代帝王朝拜、封禅之地,也是各路文人纷至沓来,争相留名之地,可以说是人文因素确立了五岳独尊的地位。 泰山已经超越了自然山川的概念,它已经是国家民族山河的另一种表达,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和信仰的象征,也成为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一切的历史人伦都会更替,但只有泰山的岩石永远存在。正如《岱史·遗迹纪》所谓:“遗址依然,文献具在,流风馀韵,与泰岱为终始,所谓旷千百载而相感者,其在斯与”。 今晚,与山外山一起感叹五岳之首的“国山风度”。 泰山,又名岱山、岱宗、岱岳、东岳、泰岳。远古时始称火山、太山,“大”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均见其形,读音为“太”。且“太山”意为“大山”,先秦古文中,“大”、“太”通用。按古文字的传统读法,“大”亦有“大”、“太”、“代”三音。春秋战国时,由于同音字的引申和同义字的演变,“太”与“泰”、“代”与“岱”,“岱”与“岳”也互相变通了,这样相继出现了“泰山”、“岱山”、“岱宗”、“岱岳”等专用名称。 “泰山”之称最早见于《诗经》。“泰”意为极大、通畅、安宁。《易·说卦》“履而泰,然后安”。“泰”字就有原来的高大、通畅之意引申为,“大而稳,稳而安”。随即出现了“稳如泰山”、“国泰民安”、“泰山鸿毛”之说。 泰山雄峙于山东中部,前邻孔子故里曲阜,背依泉城济南。在神话中其往上最接近统领“三界”的玉皇大帝,东邻便是神仙居住的仙山蓬莱与瀛洲;又雄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凌驾于齐鲁平原之上,东临烟波浩淼的大海,西靠源远流长的黄河,南有汶、泗、淮之水。 因地处东部,泰山故称“东岳”。东方为太阳最早升起之地,古人以东方为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故有“五岳之尊”美称。 周人和秦人,脸是朝向东方。考古发现,秦人的陵墓也向东方。《尚书·尧典》说,日出嵎夷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东方红,太阳升,山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山东大汶口,就在泰山的南面。它的陶器,最典型的刻画符号就是表现日出。八主祠,日出祠,祭太阳,位置在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尖上。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是成山头。登上泰山,一定要看日出,道理就在这里。五岳配五行,五行的开端是东方。泰山当然是五岳之首。 《东岳禅光》李叔平 泰山岩石的古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之最,有一种伟晶岩的年龄达到25.86亿年。此后古泰山在沉浮中造化,在距今一亿多年前的燕山运动中,隆起成为今日泰山的雏形,此后不断雕塑,覆盖在表层的两千多米厚的沉积岩层全部剥蚀掉后,由那些抗蚀性强的岩石形成峻峦高崖的形态。泰山之石,经历过中国山川中最长久的沉浮造化,堪称一片大陆的奠基。 虽然说泰山的海拔不算高,但它的绝对高度,足以让人联想到“通天”的台阶,这也是为什么古人认为泰山可以通天。金人元好问就称赞泰山为“天壤间一巨物”。 而泰山复杂的“变形”过程,又雕琢出诸多美妙的景观。岱顶的瞻鲁台、山中的仙人桥、扇子崖、飞来石,数不胜数……相传当年汉武帝八登泰山,惊叹得不成句——“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 泰山与孔子、诸子 泰山与名人结缘,肇始于孔子。孔子登临泰山,抒怀畅志,开阔胸襟;考察封禅,学习礼仪;了解民情,观知时政。明代《泰山志》说:“泰山胜迹,孔子称首。”这不仅拓展了泰山文化的内涵,也使儒家思想文化借泰山之力发扬光大。同时,孔子也开创了名人登泰山的先河。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使后人竟起仿效,接踵而至。 当年孔子曾率弟子多次到泰山登高览胜。《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礼记檀弓》则云:孔子过泰山侧,问妇人之哭而叹苛政猛于虎也;《列子》云:孔子游于泰山,问荣启期之“三乐”而善其能自宽;《韩诗外传》云:颜子从孔子上泰山,望吴阊门之系白马,而颜子对以有如系练;《孝实录》亦言:曾子耕泰山下,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 《孔子圣迹图之泰山问政》 泰山对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学习礼乐,由此得窥封禅大典全豹;登泰山而小天下,以开阔的眼界胸襟审度自己德才学识的修养;孔子临终,孔鲤,颜回、子路相继死去,自知已日薄西山,遂感发“泰山梁木”之哀歌,把自己的生死与泰山联在一起,足见泰山在孔子心目中不同寻常的地位。 孔子以泰山自况,也得到其弟子的承认,《礼记檀弓上》记:“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孟子》另一处引子贡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也”。其另一弟子有若说“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孔子在泰山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夹谷之会,是儒家政治的成功范例,证明儒家绝非“盛容服而饰辩说”、“博学不可仪世”的虚妄之徒;《龟山操》、《邱陵歌》,引出屈原、李白等人行路难的千古传唱;长期奔走齐鲁,对比中悟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似乎已涉及到文化地理对人的性格的影响;在细致的观察中体味到“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宋代的泰山书院以孔子创立的儒学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如果说有谁在山川游览中留下了最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那么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后人把孔子与泰山紧密联系在一起,誉为“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严云霄《咏孔子庙》),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孔子圣迹图之夹谷会齐》 在先秦时期,泰山就被诸子百家多次提及,成为诸子讨论的话题之一。在儒家、道家和法家学者眼中,泰山都是以宏伟髙大厚重的形象出现的。由于其髙大无比,绵延较广,泰山也被儒家学派隐喻为圣人孔子及其高深的学问,成为规避世间苛政的场所。作为齐鲁地区的神圣之山,《左传》与《晏子春秋》编者、儒家以及墨家学派都曾强调对泰山的祭祀礼仪,并且,泰山祭祀应由周王或诸侯王掌握。在纵横家的论述中,泰山成为国泰民安的象征,是齐国南新疆域的界标。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的象征《晏子春秋》中首次出现了泰山神的记载,成为拟人化的山神。战国晚期的管子学派鼓吹泰山封禅说,泰山成为祭天告地之所,封禅泰山成为易姓而王的象征。在《韩非子》中,黄帝作为最高神灵出现在泰山,战国时期盛行的黄帝崇拜已从昆仑山转移到了泰山。泰山有关黄帝信仰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时期泰山观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异。 先秦时期,泰山只是一座地区名山,地位并不显赫。泰山地位的上升,大约起于春秋晚期,它是伴随着齐鲁文化的繁荣和诸子百家的渲染而逐渐兴盛起来的。战国晚期,经过齐鲁学者的渲染和夸张,泰山的地位越来越高,渐趋独尊之势,以至于人们认为泰山自古以来地位就是最受尊崇的。降至汉代,泰山摆脱了地区性大山的意义成为五岳之长,具备了宇宙山的机能,成为大地的中心。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泰山有高人的含义:“泰山北斗”;也有驱邪镇魔的神力:“泰山石敢当”;还有人生之重的喻比:“重于泰山”,而它最高的光环在于政治象征——历朝历代皇帝封禅之地。泰山出大名,主要靠帝王。“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史记·封禅书》) 中国自古讲究“山岳以配天”,山之高大而尊者称岳,岳是名山中的名山。而泰山,是五岳之首。 《史记·封禅书》记载了远古七十二君王的泰山行,他们的“旅游”项目繁多,包括祭祀、巡狩、会盟、定大位、刻石记号。这些君王包括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特别是帝舜,在此朝会东方的诸侯,并向四面八方遥望,意即照会四方诸侯,而四方诸侯也纷纷登上本方境内的高山,向泰山遥祭,这一行为叫“望秩山川”,其背后昭示的是大一统的理念,而泰山俨然已有“国山”的气质。 《五岳真形图》 中国人自古有一番对于天地的态度: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甚至一草一木都有神灵统辖,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主宰着人的生存与命运。周代《礼记》里明确表达出:山川、林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为神。山岳崇拜随之而起。先人以为,但凡高的山,便可以与天相接。泰山之祭,来自于泰山之敬。只要看一眼泰山“天阶”那一段,自会理解为什么古人把泰山想象成可以通天的山。 七十二君王祭泰山的传说归传说,历史是历史。历史上,明确可考,真正举行过封禅大典,有六个皇帝,他们是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这六位帝王都接踵到泰山封禅致祭,刻石纪功。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泰山的神圣地位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崛起于西陲,西岳华山近在咫尺。然而,就在秦王朝建立的当年,志高意远的始皇帝便不顾鞍马劳顿,远赴东岳泰山举行封泰山、禅梁父(泰山下的小山)大典。所谓“封”,是指在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所谓“禅”,是指祭地。 秦一直被东方六国视为夷狄之国,而远古七十二君王祭泰山的历史传闻,为泰山蒙上正统的色彩。封泰山,具有在法统地理观念上征服东方地区,和继承华夏各先帝贤皇的正统帝位,这双重的象征意义。所以秦始皇才如此迫不及待。 《泰山刻石》李斯 《唐玄宗封禅图》 秦始皇之后,接踵而至的有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这些皇帝他们都背负着王朝更迭、时政转折的重担。 封禅虽说是多数皇帝的毕生追求,然而又不是任何人都能取得资格。即便皇帝没有自知之明,臣下也会秉直正告。例如齐桓公称霸后,想封禅泰山,就遭到管仲反对。管仲说,古代圣王封禅,要有十五种祥瑞出现,像东海有比目鱼、西海有比翼鸟等,现在我们没有这些,怎么好封禅呢?于是齐桓公就死心了。 其实,管子还有一层不好表达出来的意思:齐桓公虽然称霸一时,却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周室仍在,何谈资格封禅? 泰山上,琳琅满目的摩崖巨作,遍布山岩,宛如一部历史的石书。这是因为泰山首先是名垂千古的“政治山”。封禅岱岳从来都是历代帝王的经国大事。泰山因而获得无上的地位与尊严,怀揣中兴大唐梦想的唐玄宗,亲自撰书千字《纪泰山铭》,创立了帝王摩崖之最。东岳不仅在帝王生涯中起着作用,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涯里,黎民百姓的世俗生活中,同样不可或缺,于是刻在石上的泰山名号越来越多,日复一日尊崇不断在加码。 泰山岱庙廊里,有块极为别致的鸳鸯碑,又名双束碑。一顶完整的碑额之下,两块双胞胎一般的长方形碑石并立,喻比二圣为鸳鸯。这是武则天密令亲信——泰山主持道士郭行真所立,并同时建造了岱庙的前身——岱岳观。 武则天此举大有来意。显庆五年(年),高宗正式下诏,宣布朝廷大政由皇后武则天处置,谓之“二圣”。对武则天而言,皇帝的宝座似乎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她进而想到借助泰山的“神威”,为自己的登基铺垫道路。在她的授意下,先是心腹大臣李敬宗上表请封。武则天又表示要改革封禅的礼仪。在祭地这个环节,由宫内女职官来行礼。就这样,武则天如愿以偿参与了泰山封禅,昭告天下自己的重要地位,为大唐“改天换地”走出了关键一步。 在封禅史上最奇怪的一位皇帝,是宋朝第三帝宋真宗,他是一位打了胜仗还要赔款——签了“澶渊之盟”的窝囊皇帝,他封禅泰山的目的,是平息举国上下的议论。 宋真宗首先导演了一系列的戏:有天书接连降世,祥瑞连现——皇宫天空上出现紫色云彩,犹如龙凤一般,各地也纷纷呈报祥瑞出现,并上书朝廷,请求真宗封禅。凭着自己导演的祥瑞大戏,真宗终于“获得了”封禅资格…… 宋真宗之后,帝王来泰山只举行祭祀仪式,不再进行封禅。 巨幅壁画——《启跸回銮图》。绘满岱庙天贶殿的三面墙壁,但见,泰山神以天子仪卫出巡、回銮,前拥后簇,壮观不已,恰如宋真宗,大举封禅泰山的盛况。此画传为宋代始作,后世又描摹重绘。 可以说,泰山在中国古代稳固帝业、稳定政权的历史中,频频立功。仅就此而言,泰山乃是当仁不让的王朝首山——“国山”。 泰山文学 泰山的岩石杂而坚韧,这些石头还有一种特别的特征,就是多垂直节理。所以泰山的小断崖尤其多。崖面笔直光滑,是天然的摩崖圣地。受到皇帝们钟爱的泰山,同样受到文人们的膜拜。泰山文学几乎与中国文学同时起步。《诗经》中即有赞颂泰山的诗句——“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圣人孔子钟情泰山,人所熟知的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莫不亲登泰山,留诗留文。因而泰山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纪念碑。 从崇山祀岳到范水模山 关于泰山诗的源起,清初诗人钱肃润《泰山诗选序》中曾详作考论:“有客问余曰:‘泰山诗起于何代?倡自何人?’余应之曰:‘黄帝会群臣于泰山,作青角之音,未有诗。有虞氏东巡至岱宗,群臣歌卿云,卿云,言泰山云也。《卿云歌》,意者其泰山诗乎?’客曰:‘子姑言其有据者。’余对曰:‘《周颂》有之,“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班固引为周太平封泰山诗,此泰山诗之首也。’客曰:‘高山泛言山也,岳为四岳通称,非止泰岳也。’余曰:‘微子言,吾亦疑之,吾与子专言泰山诗可乎?《鲁颂》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是诗也,实为泰山赋也。’”此为今知最早关于泰山诗源之论。 确如钱氏所论,最早出现的泰山诗作,与“昉于虞书”、“见诸周制”(高怡《泰山道里记序》)的上古山岳崇祀紧紧相连。《诗经·鲁颂》“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这一最早专咏泰山的诗句,出自鲁国宗庙诗《閟宫》之中,既是对鲁之首“望”(《公羊传》称鲁有“岱河海”三望之祭)的礼赞,同时也是对“鲁侯之功”的颂扬,充满了宗庙祭典的庄重肃穆。更早于此的《周颂·时迈》,诗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之词,据唐儒孔颖达疏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诗中之“乔岳”显指泰山而言,《时迈》开启了泰山封祀诗的源头。 另一首《周颂·般》则描摹周天子登山而祭的场景:“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据明人汪坦考证:“按《虞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其至于南、于西、于北,皆如《舜典》。则谓是诗为登岱而颂,无不可。’”(汪坦《诗般跋》,刻于经石峪)这些诗中所体现的,均是山岳崇祀的庄严与国家祀典的盛大。因此可以说,最早的泰山诗是以宗庙祭祀诗的面目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 汉魏六朝时期的泰山诗作,已逐步开始有了对山川自然形象的描摹,如的“隆高贯云蜺,嵯峨出太清”(曹植《驱车篇》)、“峻极周以远,层云郁冥冥”(陆机《泰山吟》)、“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谢道韫《泰山吟》)、“岞堮既崄巘,触石辄迁绵”(谢灵运《泰山吟》),但这些诗句均缺乏对山水形态的细致观察与具体状摹,即便是谢灵运这位“山水诗之祖”,其咏岱之作也未尽脱前人窠臼。此期的泰山诗歌中,仍充斥着山岳崇祀与鬼神信仰的色彩。如“幽岑延万鬼,神房集百灵”(陆机《泰山吟》)、“登封瘗崇坛,降神藏肃然”(谢灵运《泰山吟》)。 《泰岳松风图》王翚 惟是汉魏之际,由于受泰山道教兴起的影响,在曹操、曹植父子的泰山诗中,出现了“仙人玉女”等意象,变鬼城为仙府,成为泰山游仙诗的先声。总体看来,当山水诗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一种文学思潮在南方滋生并形成时,泰山诗作却由于地理因素(地处北方),并未能感染这一时尚诗风。 唐代被认为是“中国山水诗的巅峰时代”,但泰山山水诗的创作却“姗姗来迟”——开元之前的泰山诗主题,仍是“鞭挞走神鬼,玉帛礼山川”(马友鹿《陪敕使麻先生祭岳诗》)、“石闾环藻卫,金坛映黼帷”(李义府《在巂州遥叙封禅》)的祀岳之咏。较早以彩缣铺写山川的李白《游泰山六首》,虽不乏“使人有雄飞啸傲于岳巅之想”的神来之笔,但充轫篇中的仍多飞仙玉女,从内容上诚如明人所云:“六首俱主在求仙,音调亦本郭景纯《游仙》。”(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可看作是泰山神仙诗至山水诗的过渡之作。 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者,则当推杜甫之《望岳》。关于此诗,前人有过一番精彩评述:“少陵以前写泰山者,有谢灵运、李白之诗。谢诗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浅。李诗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复。此诗遒劲峭刻,可以俯视两家矣。”(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更为重要的是,杜甫咏岱之作,已从山岳神仙中完全摆脱出来,目光由阴森鬼府的崇拜,转入对神秀青山的审美。促成泰山诗创作主题的转向——自子美伊始,祀岳祭曲虽一直延续(明清时仍不乏此类题材),但作品主流却转向对自然景观与人文胜迹的咏颂。 杜甫以“望”入题总摄全岱,后世诗人更多写“登”,侧重对具体景观的摹绘,如李德裕与韩偓以“沧海似熔金,众山如点黛”与“直须日观三更后,首送金乌上碧空”之句,开日观诗之先。此后模山范水,藻饰山川,华章云集,泰山诗面貌顿为之一变。而这,也正是杜甫《望岳》一诗的历史贡献所在。 从怀古咏史到歌风纪俗 融怀古入山水之作兴于晚唐,“晚唐诗人多喜欢反思历史,……也因为如此,在同前人一样吟咏山水的同时,多一重历史反思的沉潜理性”(陶文鹏等《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以泰山为题的咏史怀古诗,始于晚唐胡曾《咏史诗》中之《云云亭》:“一上高亭日正晡,青山重叠片云无。万年松树不知数,若个虬枝是大夫。”云云亭系封禅大典中禅地之所,作者借此起兴,并特笔咏怀五大夫松故事。此作与胡曾《咏史诗》整体风格一致,“其主旨在于追述兴亡,托古讽今,意存劝戒”(赵望秦等《古代咏史诗通论》)。 五代徐寅《大夫松》:“争如涧底凌霜节,不受秦王号此官。”借咏秦松寓其惓惓旧朝之感。宋初李昉则借无字碑反思秦亡汉兴的历史,其《题岱宗无字碑》云:“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千山。不因封禅穷民力,汉祖何缘便入关?”皆为泰山咏史诗中开派之章。自此,对帝王封禅史迹的慨叹,对圣贤遗躅的追怀,成为泰山诗创作的重中之重。 以“长松不改登封色,残碣犹存秦汉歌”(王暏《登岱》)为主调的怀古咏史之作,在元明清泰山诗中成为主流。但就在一片黄钟雅乐之中,也不时夹奏着俚曲时调——这便是明中叶后出现的大量歌风纪俗之什。“宋元以后,随着碧霞元君信仰的广播域内,一时涌现出一个泰山进香的高潮,泰山文化舞台的主角转为下层民众,致使此时帝王、文人的泰山活动也莫不受到民风民俗的濡染。这一历史时期,可称之“民俗山”形成期。”(周郢《泰山与中华文化》)此番社会变革,也深深影响到泰山诗的发展走向。最早将其引入诗题的,为宋人苏辙《游泰山·岳下》,但应和寥落。 《泰岱览胜图》黄鼎 自觉实现此一创作重心转变的,则是明清诗家,特别是公鼒与李林两家之岱诗,他们将目光之处投注到当时风靡天下、万众匍匐的进香新俗,不咏“天门日观、秦封汉草”,而是目光投注于“担囊策杖忘家子,叫佛呼天折臂翁”,诗笔实录“玉妃似得东皇宠,五百年来震位崇”、“泥金甲马绢包头,楚服吴音遍九州。只为大罗真有路,因教少妇不知羞”等风俗万象。而李林则更进一步,提出应创作能传播于进香大众的应时之谣,“只好风谣翻旧谱,沿途教与进香人”,使泰山诗创作通俗化、普及化。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明中叶以后的泰山诗重心再为一变。 明清时期的歌风纪俗之作,最为突出的是对明中叶以后兴起的香社活动生动摹写。这其中或描画香社信众千里奔走:“岁云暮矣当丰年,香火逐群礼泰山。半夜鸣金催社侣,踏星靡靡霜花斑。千声一佛潮音吼,甲马咸云神掖走。闺中严属戒腥荤,梵宇琳宫遍稽首”(高珩《朝岱》);“鼓渊渊,旂扬扬,庄农男妇来烧香。风雨栉纚不辞苦,号佛彻夜声悲凉。千里茧足走,百里裹粮糗。但愿见金身,争先惟恐后。旅馆招摇飞市虎,榷钱横嚼无人语。山头争拜碧霞宫,一霎金帛堆尺许”(于振翀《进香客》);“士女齐驱拥道旁,鸣钲击鼓列成行。胸悬朱匣描金就,尽说朝山进瓣香”(张永铨《山左竹枝词》)。 或描述元君各祠香火烛天:“更配碧霞君,庙貌遍天壤。结队称进香,男女纷来往。税课抑不止,终日万人上”(邱嘉穗《岱下感怀二首用壁间韵》);“夜深号佛买长香,上下林峦列炬光。将到红门声更沸,东西路合岱宗坊”(纪迈宜《泰安进香词二十七首》);“梯山航海同奔驰,车尘马足春台熙。老幼男妇相扶持,铜钲一声搴红旗。祈福介寿求佳儿,秋禾满车麦双歧。年年施钱碧霞祠,尔去钱无知不知”(徐宗干《香客行》)。 或实录香客店场景:“焚香申祷祀,侵晓出闉闍。(注:逆旅主人多奉泰山神,将登山,必先致告。)”(赵怀玉《登岱七十韵》)同是写泰山,由于视角转换,将山水诗变为风俗诗。 从借景喻道到精神揭示 正如昔贤所云:“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宋思仁《泰山述记》卷七)从“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到“仁道在迩,求之若远”(托名孔子之《邱陵歌》),无不饱含人生哲思。而魏晋以还,山水诗成为“玄学温床的宁馨儿”(陶文鹏等《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诗人力求在山水中寄寓对宇宙人生与自我奥义的新认识。这一创作理念,也促使泰山诗带有更多的玄哲气息。 若从唐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算起,历代此类即景悟道之作可谓更仆难数:其或激发人生壮志,如“宁不念崎岖,怀此久且亟……频语鲁诸生,万仞在自力”(邹善《登泰山》),“绝顶遂攀跻,始知天地广”(王遴《玉皇顶》),“大观荡尘襟,敢辞登陟艰”(朱节《登岱》);或悲慨世途艰辛,如“天门咫尺君应见,似比人间路更难”(于慎行《登岱八首》);或感悟人生价值,如“我亦有身偏自重,舍时除是为君亲”(王越《舍身崖》),“此行不了封侯业,愿作顽躯窃比君”(文颖《过泰山》); 或洞察名利虚幻,如“私哂名利心,蹩躠竞何益”(李濂《游吕公洞》);或领悟治学境界,如“登高必自卑,学问宁有佗”(郑鄤《读孔子〈邱陵歌〉》),“即景悟为学,无穷戒株守”(乾隆帝《朝阳洞》);或参悟禅宗佛理,如“由来最上乘,原不立文字”(邹德溥《无字碑》)等等,无不具有一种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闪烁着哲理的光华。 《泰山旭日》黑伯龙 不过,上述诸诗多属于“以景媚道”之作,也就是作者借登山临水叙说其哲理体验,而非(也无心于)对泰山本身精神内涵的把握与揭示。自宋元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悟道”诗,所感悟者乃是泰山之精神内蕴,这与前述喻志之诗艺术上虽无高下之分,却与泰山主题更为贴近。 此类诗作似始于宋人石介。石介《泰山》诗云:“七百里鲁望,北瞻何岩岩。诸山知峻极,五岳独尊严。寰宇登来小,龟蒙视觉凡。此为群物祖,草木莫锄芟。”关于此诗的文化意义,刘凌先生在《“五岳独尊”探源》中曾予以准确揭析:“尽管唐玄宗《纪泰山铭》中已有‘五岳之伯’赞词,但明确以‘五岳独尊’称扬者,却首见于石介《泰山》一诗。……诗中透露出泰山‘独尊’的两个主要依据。一是泰山体量之大。‘岩岩’乃空间形象,高峻貌。二是泰山存在的时间之久。‘祖’有‘初’、‘始’等义,为时间概念,也可引申为事物根本、母体。……正是这种时空特性,赋予了泰山特殊的威严和神圣感。”(刘凌《反思传统·重识泰山》)而石介对泰山这一特质把握,实基于其生长岱下、讲学岱阳的人生经历,使其对泰山文化内涵有更深刻的体验与认识,最终在诗笔中凝结成“五岳独尊严”这一震烁古今的咏岱名句。 继石介之后,进一步对泰山内蕴作出精彩诠释者,当推金元之际郝经的《泰山赋》。赋中写到:“粤惟兹山,首出庶岳。……孰如兹山,中华正朔,建极启元,衣冠礼乐。天宇夷而嗥嗥,王道裕而绰绰。……孰如兹山,衮冕黻珽,朱弦疏越。纯粹中正,崇高溥博。”郝经通过铺陈扬厉的辞笔,将泰山与海内诸山遍作比较,从而将泰山推为国中第一名山;更为特异的是:他以“中华正朔,建极启元”的非凡之辞,将泰山视为中原文明的总体象征与具体代表。在泰山诗赋史上,郝经此篇值得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