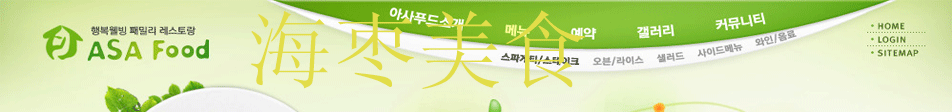|
忆那年我刚上中学,学校正落在市中心,和友人最常逛的便是步行街一带。记忆里,每逢周末,都能遇见一挑担提盒卖面塑的老人,他的双手真是神奇,能把花鸟草虫各式人物,揉弄得神采飞扬,插满木盒。孩子们常扎了堆围挤着欣赏,看雀儿振翅,雄鸡打鸣,毛虫蜷在梧桐叶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个孙猴儿,身着红袄,腰系皮裙,头戴金冠,两翎彩羽随风舞动,左手持金箍棒,右手捉大蟠桃,真真像极。 如今,我虽久未见老艺人露面,倒是有幸结识了金坛五叶潘家面塑的第五代传人——潘俊芳老师。如此机缘似一根丝线,悄悄扯出儿时回忆,让我迫不及待前去探访。 寻潘老师很爽快,对于我唐突的拜访未有丝毫不快。早九点,气温攀高,她早早来到小区门口迎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潘老师,朴实而温和,她笑了笑,“这天真够热,快跟我走吧。” 潘老师家中很是整洁,唯独门前一张方桌上很是杂乱,散落着面塑制作所需各式工具。 一些面人刚刚动工,看得出是古装女子,初具身形,腰肢婀娜。“这些还都是胚子,刚捏出形体和头部,准备做麻姑献寿,百花仙子,寓意十分吉祥。” 制潘老师通常一次性揉一大块面团冻在冰箱,需要用时再取出加热。现在面塑主要分为两类用途,一类收藏,一类食用。“过去,但凡结婚喜庆、满月百岁、烧七祭祀、甚至上梁大吉,都会请来手艺人制作面塑,现在少了,更多人是买回去当艺术品欣赏。” 用到什么颜色的面团,她都需要在蒸好的面团中加入不同颜料再反复揉搓。“染料颜色越来越艳丽,但同时也不易清洗,换次颜色洗次手。用了不好的染料,面人还容易变色干裂。”潘老师说。如今,偶尔会用彩泥揉进面团就方便干净多了。 面塑制作需要各式工具,更需掌握“一印、二捏、三镶、四滚”等多种技法,做到形神兼备并非易事。据说,从前的工具材料更多,木头、铁、竹子、塑料,甚至还有用骨头做的。 看着这么多传神的面人儿,我好奇,“是不是需要美术功底?”“相比于深厚的美术功底,做面塑更需要的是多观察勤练习。”潘老师成长于面塑世家,是家中长女,下有一弟一妹,唯有她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幼时,她最多的娱乐便是趴在桌前,跟随父辈学做面人。期间遭逢文革,面塑连同其他许多手艺一同经历劫难,许久才敢公开为人做面塑。文革结束至今,赖社会清明,这一度消失的传统手艺,才又渐渐恢复。 人常说,一切手工技艺,皆由口传心授,耳濡目染多年,潘老师从一只桃一朵花,做到一只鸟一条鱼,再做到时而妩媚,时而风情,时而俏皮活泼的人物。愈发精致的面塑中,有她用心讲述的故事情节,还有悉心揉碎掺入的几十年光阴。 潘老师开始制作裙摆。与一层层往下削的雕刻相反,面塑需要一层层往上堆。文的胸、武的肚、老人的背脊、美女的腰,搓揉捏挑天上景,喜怒哀乐人间情,个个都有讲究。只有把裙摆按压的薄而服帖才不易干裂变形,她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高。 蠢蠢欲动的我尝试着学制了朵玫瑰。为防面沾手,先要抹些护手霜。老师手中的面团仿佛有生命,稍加揉搓已有模有样,到了我手中,面却成了“死”面。 面塑制作着实没我想象中那么简单,与幼时捏橡皮泥更有天差地别。 赏踏进储藏室,我仿佛成了刘姥姥。先看这金陵十二钗,臂中披帛一悬,半肥半瘦;纸鸢当空,且喜且嗔……细看个个都是苗苗条条的身材,丰丰满满的前胸,清清秀秀的面容,真是惟妙惟肖,灵动鲜活。 金陵十二钗 麻姑与寿星 孟母教子 关云长 人参娃 迎春 惜春 还有孩子最爱的卡通人物、十二生肖等。精致到头发丝的手艺直让人拍案称绝。 相对于北方面塑的古朴、粗狂、豪放,潘老师的风格更显细腻精巧,据潘老师介绍,她并未细究过朝代服饰,抛弃条框,如何好看如何设计。 人近中年,她反倒有了一套被岁月催熟的独特审美。 面塑,也是门关于“美”的艺术啊! 叹小憩片刻,和潘老师谈到面塑,谈到传承,很是感慨。面塑的学习和制作很是耗费时间精力,手掌大小的古装人物做完善至少也需要一个整天。为了专心制作面塑,潘老师辞了工作,一心扑在这项非遗文化上。接下来,潘老师还将代表金坛,参加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的面塑比赛。 周末但凡空闲,她还会去文化馆、三中、金沙、常州民俗学校等地方为学生授课。“学的人多,坚持下去的人很少。面塑看起来简单,但其实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做后盾。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有这个时间和耐心啊。”潘老师无奈且焦急。 后经了解,步行街一带久未露面的老手艺人,早年罹患癌症已经去世,生前传承的弟子们也在他去世后四散离去。 步行街的老人,随身携带的老木匣,满匣的面人,气宇轩昂的齐天大圣,永远只能在我的记忆中留存。 可现在, 我知,金坛面塑仍有人在学,仍有人感兴趣, 我知,薪薪之火仍在诸如潘老师这类人的坚持中代代传递, 我知,如此瑰宝,绝不应经历汉朝至今千百年历史后戛然而止, 真心希望包括金坛面塑在内的所有非遗文化都能生生不灭,脉脉相传。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