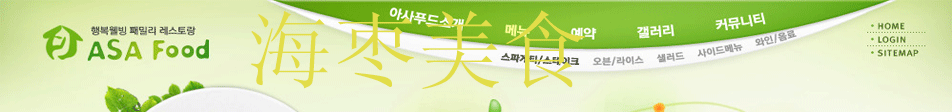|
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起,至清代雍正乾隆之际的《龙藏》止,我国在19世纪以前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印制的汉文佛教大藏经有十几种,再加上20世纪前几十年用铅印方法印制的《频伽藏》和《普会藏》,我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印制的汉文佛教大藏经总计近20种。每种大藏经对佛教典籍的传播、佛教的发展,以及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大藏经中,我认为最有特点的是《嘉兴藏》(也称《径山藏》、《方册大藏》)。近几十年来有许多文章和书的有关章节对《嘉兴藏》做过介绍,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是不全面的或不准确的。从年起,我对《嘉兴藏》在海峡两岸的存藏情况进行了调查,征集到了各个藏本的子目,查阅了有关的目录,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辑,工作已接近尾声。现将我了解的《嘉兴藏》及我的重辑工作介绍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原藏情况 1.刻藏经过 万历初年,明代著名高僧紫柏(真可)有感于《永乐南藏》版片已经模糊,不能再印,而《永乐北藏》版片藏在皇宫内,请印不便,认为应该由民间新刻一部大藏经。又认为以往的大藏经多为梵夹装,不仅刻印的成本高,而且装帧和携带都不便利,新刻的大藏经的装帧应变梵夹为方册,这样可以使佛教典籍广为传播,即使遇到乱世,因传播广泛,也易于典籍的保存。紫柏大师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几位高僧及居士陆光祖、冯梦祯等人的赞同。于是于万历七年()开始在五台山试刻,刻了《寒山子诗集》(编在续藏的第44函),万历八年刻了《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会译》(编在续藏的第31函)。经过几年认真的在各个方面的筹划和准备,于万历十七年在五台山的妙德庵、妙喜庵开始较大规模的刻经。因为在五台山刻经存在许多困难,刻了数百卷后,万历二十一年,刻经地点迁到浙江的径山,已刻的经版也一并运往。迁到径山以后,依紫柏大师和冯梦祯的意见,决定在余杭径山的寂照庵藏版印刷,在嘉兴的楞严寺请经发行,刻经地点则分散在浙江、江苏两省的余杭、嘉兴、金坛、吴江等地的一些寺庙。 万历三十一年()紫柏大师罹难死于京城,刻藏之事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幻予、澹然、念昙等和其他僧人(如江西的性宗等)相继主持,他们都得到了各地僧人和居士的支持和帮助,使刻藏事业能继续下去。由于缺乏资金和明清之际社会动乱等原因,刻藏的时间拖得很长,大体上经过五至七代僧人和居士的努力,历时年左右,至康熙末年大规模的刻经活动才结束。如果算上个别品种的补刻时间,至乾隆时才完全结束(北京故宫藏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均有雍正时补刻者,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有乾隆时补刻者)。 2.全藏规模 《嘉兴藏》总共刻了多少种释家典籍,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据北京故宫藏本及姑且视为全藏目录的《经值画一》考察,全藏应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正藏基本上是据《永乐北藏》刻的(台湾蔡运辰先生考证个别品种略有出入)。可以说正藏部分在收录释家典籍上与此前的各种大藏经大同小异,从内容上基本可以反映此前的各种大藏经。续藏、又续藏两部分收入的释家典籍几乎全是我国僧人和居士的著述,是此前其他大藏经所无的。紫柏大师在《刻藏缘起》中虽然没有说明,但实际上增刻续藏、又续藏两部分,应该是他重新刻藏的主要目的所在。他在倡议刻藏时,对刻续藏、又续藏应该是有计划的,这从前面提及的万历七年和八年刻的两种典籍分别被编入续藏的第44函和第31函,就可以得到证明。《嘉兴藏》收典籍的种数和止刻的具体时间之所以难以确定,主要在续藏、又续藏两部分上。紫柏大师罹难后,刻续藏、又续藏的计划不断被后继的主持者所突破。既然这两部分所收的是“本土著述”,而刻藏又迟迟没有终止,后继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意愿有所增入。这两部分收入了很多明末和清代顺治、康熙时僧人和居士的作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这两部分的编辑与排序,更是出自后继者之手。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清圣祖玄烨在南巡之时来到径山,对刻藏之举会有所了解,也许还看过刻完的经版和印好的经册,这对径山的寺庙和主持刻藏的僧人来说是很大的荣幸。因为这一点,在全藏基本刻竣之时,主事的僧人决定用白绵纸将现存的经版刷印一部,精心装潢,进呈给皇帝。这便是今天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该藏。这部《嘉兴藏》除乾隆三十四年()奉旨将钱谦益撰的《楞严经疏解蒙钞》2函10册撤出外,其他基本保持刷印进呈时的原貌,即正藏函,收书种,卷,用《千字文》编序,始“天”终“鱼”,续藏90函,收书种,卷,又续藏43函,收书种,卷。这个数字基本成为许多人在著作中介绍《嘉兴藏》所列举的数字。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杨玉良、邢顺岭二位同志对该部藏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著了《故宫藏嘉兴藏目录》上下两卷,油印行世。 佛教典籍是提倡流传的,信徒把传播经书视为功德。《嘉兴藏》刻完的经版汇集到径山之后,经常有人去刷印,因价格问题和拖欠银两问题,刷印者常与寺僧发生争执,甚至诉讼到官府。于是官府下令,寺僧对刷印每种经书要明码标价,刷印者不得拖欠银两。因此,主事的寺僧编制了每种经书刷印、装订的价格表,即为《经值画一》。《经值画一》从万历时即开始编制,随着经版的增加和物价的变动,不断增补修订。现在社会上流传较多的《经值画一》,是年北京刻经处据康熙十六年的《经值画一》翻刻的(又称《嘉兴藏目录》),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每部分按函号排列,每函依次列书名,书名下列卷数和册数(相当一部分缺卷数或册数,甚至皆缺,尤其是续藏、又续藏两部分),下列价格,正藏部分按函标《千字文》。 用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与《故宫藏嘉兴藏目录》核对,二者的函数相同,子目的排序也基本相同,但子目品种有出入。故宫藏本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演义钞》等26种书《经值画一》没有,而《经值画一》中的《番字药师F72B璃光七佛功德经》等13种书故宫藏本没有。这说明对雕刻的全藏来说,故宫藏本是个残本,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是个残缺的目录。 光绪十一年(),杭州朱记荣的朱氏槐庐刻印出版了《行素堂目睹书录》,该书录共十集,其中的壬集、癸集为《藏经目录》,据前面的文字,底本是康熙时的《经值画一》。正藏部分基本与民国九年本同,只是个别子目品种互有缺无。续藏、又续藏两部分则差异很大,续藏为94函,比民国九年本多出4函,不仅有些书的归函不一,还有9种书是民国九年本所无的,也是故宫藏本所无的;又续藏部分虽然也是43函,但子目品种却出入很大,比民国九年本少数种,多出近30种,故宫藏本少数同朱氏目录,多数同民国九年本。这说明《经值画一》的版本也不只一个系统。应该指出的是,在几种朱氏目录有而故宫藏本无的子目书名下面,注明“腐烂候刻”,说明因书版已腐烂,所以给皇帝刷印进呈本时没有刷印。 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蔡运辰先生编著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其中关于《嘉兴藏》的著录续藏为93函,又续藏为46函,还有“藏外”7种。不仅函数、结构与故宫藏本及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不同,子目品种的出入也很大。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嘉兴藏》的选本,16开精装40册,书名为《明版嘉兴正续大藏经》。正藏部分10册,只选书种,续藏、又续藏部分30册,凡搜集到的几乎全印了,收书种,有几十种不见于故宫藏本和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看来影印出版的重点在续藏、又续藏上。 杨玉良同志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3期上发表了《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一文,该文的第五部分也谈到了几种《嘉兴藏》目录收书情况的不同。 据我了解,海峡两岸有十几个单位收藏此藏,其子目品种的数量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为最多。其他单位的藏本虽然在子目品种数量上比故宫藏本和有关目录少,但有些品种是故宫藏本和上述列举的目录所无的。如辽宁省图书馆藏本的康熙五年刻的《列祖提纲录》42卷、康熙三十三年刻的《五峰纬禅师关东语录》17卷,又如青海省图书馆藏本的万历二十三年刻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纂注》10卷。类似的情况在云南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藏本中也有。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现存的各单位藏的《嘉兴藏》没有一部是全的,现存的种种关于《嘉兴藏》的目录没有一种是完整无缺的。所以说《嘉兴藏》从始刻至止刻,总共刻印了多少种佛教典籍,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甚至还可以推断,从来就没有发行过,因此世上也不可能存在一部从始刻至止刻的全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几代人相继主持,刻经计划在不断变化,刻经规模不断扩大。 第二,刻经的时间过长,后面的经版还没有刻完,前面刻完的经版有的已经腐烂,而又没有及时补刻。 第三,刷印的时间不一,有的甚至是多次刷印汇集的。 第四,后继的主事者因某种原因,对个别书的结构做了调整,使早印本与晚印本的结构不同,子目的品种不同。 如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有《藕益大师佛学十种》(明释智旭撰),为明崇祯刻本,包括10种子目:①妙法莲华经纶贯1卷;②教观纲宗1卷释义1卷;③梵纲经忏悔行法1卷;④毗尼后集问辨1卷;⑤学菩萨戒法1卷;⑥菩萨戒羯磨文释1卷;⑦重定授菩萨戒法1卷;⑧菩萨戒本经诵1卷;⑨性学开蒙1卷;10梵室偶谈1卷。而北京故宫藏本无《藕益大师佛学十种》,但在又续藏第21函有《律要后集六种》,包括《菩萨戒本经》和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的《藕益大师佛学十种》中的③④⑤⑥⑦,为康熙重刻本,而⑨10两种在续藏第83函,仍为明崇祯刻本。类似这种情况还有。 第五,《经值画一》先后由不同人编制,前后缺乏照应,出现了不同系统。 3.《千字文》的应用 梁代周兴嗣一夜之间编成的《千字文》,使一千个字不重复,每个字都有固定的位置。这个特点使之成为给物品和文献编序的工具。从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开宝藏》开始,所收的经书即用《千字文》编序,形成惯例,以后的《大藏经》皆用《千字文》为藏内的典籍编序。 《嘉兴藏》正藏部分使用了《千字文》编序,因为是以《永乐北藏》为底本,所以《千字文》的使用情况与《永乐北藏》基本相同。《永乐北藏》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敕命雕刻的大藏经,永乐十九年()在北京开雕,至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刻竣,《千字文》始“天”终“石”。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二年()又补入三十几种典籍,《千字文》用到“史”字。又从《永乐南藏》补入了《永乐北藏》所缺的《续传灯录》36卷、《古尊宿语录》48卷、《禅宗颂古联珠通集》40卷、《佛祖统纪》54卷,类别名称为“北藏缺南藏函号附”,此四种书用的是《永乐南藏》原有的《千字文》,分别是:合、济、弱、林,密、勿、多、士,鸡、田、赤,城、昆、池、碣,此15个字在《永乐北藏》和《嘉兴藏》正藏的《千字文》编序中各使用了两次,重复使用。 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的正文前有“藏函号字附”,列出了正藏用的《千字文》,从“天”至“鱼”共个字。正文最末的“北藏缺南藏函号附”部分含书5种,除上述《续传灯录》等4种外,还有“《密云禅师语录》四本”,上有“鱼字号”三个字,说明《千字文》用的是“鱼”字。北京故宫藏本在此部分也有此书。《故宫藏嘉兴藏目录》著录此书为“十二卷,明释园悟撰,清释道忞编,附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一卷,清钱谦益(法名槃谭)撰,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一卷年谱一卷,清释道忞撰”。按,明万历十二年补入清人的著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清人著作更不可能编入《永乐南藏》,年线装书局影印出版的《永乐北藏》在“北藏缺南藏函号附”部分无此书。 此书一定是《嘉兴藏》康熙时编辑者误入的。既然此书已误入正藏,且编序为“鱼”字,只能以讹传讹,《嘉兴藏》正藏部分用的《千字文》是始“天”终“鱼”。正藏部分对《千字文》的使用大体上是每10卷用一个字。 续藏、又续藏两部分初意也是想用《千字文》编序,续藏最前的两种书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演义钞》8卷和《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80卷,辽宁省图书馆和台湾中央图书馆的藏本前者版心下刻有“天、地、玄、黄、宇、宙、鸿、荒”8个字,后者版心下刻有“日、月……鸟、官”70个字,所附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等4种文献版心下刻“人、皇”2字,二种书共刻了《千字文》前80个字。也许最初续藏、又续藏的编者对这二部分的规模没有掌握,以为不会超过卷,所以差不多一卷用一个字,为了与正藏对《千字文》的使用相区别,改正藏的阳文为阴文。也许书序没有编定和规模在不断扩大,按一卷一个字的标准已不可能容纳,除这二种书外,其他书版心下再不刻《千字文》了,只留有木钉,待以后补刻。 4.特点与价值 对于其他汉文大藏经来说,《嘉兴藏》有下述几方面的特点和价值。 第一,在装帧上改卷轴装、梵夹装为方册线装。《永乐北藏》及其以前的汉文大藏经皆为卷轴装和梵夹装。明代中期以后,我国书籍的装帧已盛行线装。这种装帧形式制作方便、修补方便、携带方便,有很大的优越性,与梵夹装相比,容量增大,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便于典籍的流通。紫柏大师顺应历史发展,改大藏经的装帧形式为线装,可以看出他具有改革精神,非常开明。这一改革,对以后佛教典籍的出版有很大影响。 第二,版式行款比较统一。一般为四周双边,边栏外粗内细,白口,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早期刻本也有四周单边或左右双边者,也有七行十七字、八行十七字、九行十九字、十行十九字、十一行二十字者);万历初年所刻的字体有的是手写体,万历末年以后刻的字体趋于横轻竖重的宋体方字,因写工、刻工匠人的不同,其风格也略有出入;版心上方一般皆刻“经”、“律、“论”、“西土撰述”、“支那撰述”等分类名称,中间刻书名及卷次,下方刻《千字文》的某字或墨钉;版框高为23至24厘米左右,宽为14至16厘米左右,书品较为宽大。虽然因刻书时间和刻书者的不同,风格有所差异,但熟悉者一看即知是否为《嘉兴藏》中书。 第三,是迄今为止收佛教典籍数量最多的我国出版的汉文大藏经。仅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的数量计算,共收佛教典籍种,这个数字是我国出版的其他汉文大藏经所不及的。正藏部分可略等于其他各种大藏经,其特点和价值最主要体现在续藏、又续藏上。这两部分收录的是中国僧人和居士的著述,有的是对译经的诠释,有的是关于佛教的专著,还有用佛家思想对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诠释,如明释智旭撰的《周易详解》及明释憨山撰的《庄子内篇注》,而数量最多的是明末和清代顺治、康熙时期诸高僧的诗文集和语录。这些著作,有许多是因为刻入《嘉兴藏》社会上才有传本。 这些著作体现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及其特点,是研究我国佛教及其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客观地说,不可能所有有造诣的僧人都写出关于佛教的著作,但他们在多年的修行中对佛教和社会会有很深的认识,便用诗文和语录表达出来,传授给弟子。这些诗文和语录的著者,遍布全国各地,全面地反映了明清之际我国各地佛教发展状况。这些诗文和语录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佛教的内容外,还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和其他的学科领域,因此也是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的重要资料。 第四,该藏大部分书的每卷末尾都有刻书的牌记。这些牌记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捐刻者的姓名、官衔、所在地域;涉及到捐刻的原因和捐资的银两数额;涉及到所刻的经名、卷次、字数和版片数量;涉及到写刻工匠姓名、刻书时间和地点。总之,为我们了解该藏的刊刻情况、研究明末清初的出版史、研究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其他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如:从捐刻者来分析,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既有朝廷的高级官吏,也有下层的普通百姓和僧侣,可见主持刻经者为了募集资金,进行广泛宣传的情况;该藏的明末刻本中有相当数量是著名出版家毛晋捐刻的,也是由汲古阁刻的,这在过去一些介绍毛晋及其汲古阁刻书情况的著述中是很少提及的;如果认真分析捐刻者所捐银两和他们所捐刻的版片数量和字数,可以得知当时刻书的成本价格,如果再与《经值画一》的“销售”价格相比对,可以得出成本价与销售价的差额。关于该藏牌记的价值,杨玉良同志在《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一文中论述颇详。 二重辑工作 如上所述,《嘉兴藏》是很有特点、很有价值的,在经济、文化、学术空前繁荣和发展的今天,应该整理出版。北京径山藏研究中心和北京民族出版社决定按原开本大小影印出版该藏,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责成我负责编辑工作。我认为要影印出版该藏,应该做到两点,其一是把该藏现存的子目尽可能地搜集全,其二是要尽可能地保持原貌。要做到这两点,既不能完全以某一藏本做依据,也不能完全以某种目录做依据,必须重辑。重辑工作的第一步是搜集各单位所藏该藏的子目。我先后征集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苏州西园寺(藏书单位后来有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华岩寺的藏书)、云南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单位藏本的子目,又从有关目录中摘抄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单位藏的子目,又获得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中关于《嘉兴藏》的目录和《明版嘉兴正续大藏经》的目录。非常感谢各藏书单位的有关同志,当他们了解了我的目的后,立即将子目寄来,有的甚至是重新做。许多热心的同志知道我在重辑《嘉兴藏》,向我提供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使我征集子目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重辑工作的第二步是核对各单位藏本的子目及各种目录。将《故宫藏嘉兴藏目录》每种书做一张卡片,按顺序排好,再将其他单位藏本的子目逐一与故宫藏本的卡片核对,在卡片上记录是否有藏及其异同,再用各种目录所著录之书也逐一与故宫藏本的卡片核对,故宫藏本所无者则另制一张卡片。这样核对完之后,每种书哪些单位有藏,哪些目录著录,哪些品种故宫藏本无就一目了然了。 重辑工作的第三步是进行编辑和选择底本。我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藏本应该是最后一位主持刻藏者在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刷印进呈给皇帝的(该藏本有确切的刻经年代最晚者为康熙四十六年,又有雍正时补刻者),三百年来藏所固定,没有因社会动荡而受到损坏,函册编排有序,基本保持了原藏的原貌,民国九年北京刻经处刻的《经值画一》,虽然在子目品种上与故宫藏本有出入,但函号与故宫藏本完全一致,书序也基本一致,二者相结合可做为重辑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做法是: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皆按故宫藏本的函号、书序编辑;正藏部分故宫藏本所无者,按《千字文》的字顺编入相应的函和相应的位置;续藏、又续藏部分故宫藏本所无者,如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中有,据其所在的函号和书序,编入相应的函和相应的位置,民国九年本《经值画一》也无的,则编入“拾遗”,为了编辑方便,“拾遗”部分按藏本单位相对集中编函。分析有关《嘉兴藏》的资料,原编者的初衷只是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似乎没有编三部分之外的计划。我认为既然已列入《嘉兴藏》计划刻的书,实际已是该藏中书,不宜称之为“藏外”,“未入藏”等名称,所以我称之为“拾遗”,是对续藏、又续藏两部分的拾遗,因为没有确切依据归属,只能这样称谓。对多个单位皆有藏本的品种,在底本的选择上是择善而从,如有缺叶,用其他藏本补;对只有一个单位有藏本的品种,则无选择余地了。 重辑工作的第四步是续配《千字文》。正藏部分是有《千字文》编序的,续藏、又续藏及拾遗三部分没有。我认为既然是同一部大藏经,应该有统一的《千字文》编序,所以决定给续藏、又续藏、拾遗三部分续配《千字文》。正藏部分没有使用的字还有从“秉”至“也”,共个字。如果用正藏部分每十卷一个字的标准续配,个字显然不够,只能根据续藏、又续藏、拾遗的函数、卷数、册数综合考虑,个字适当分配。因为是影印出版,又要保持原貌,续配的《千字文》只能印在每册的封面上。重辑的《嘉兴藏》把《千字文》一千个字用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字文》编序。 重辑的《嘉兴藏》,尽我的能力把能搜集到的子目书都编进去了,应该是一部自《嘉兴藏》刷印以来收子目品种最多的该藏。但仍不是从始刻至止刻的全藏,一是因为没有完整无缺的目录可参照,二是因为有些子目品种见于有关目录,而不知藏于何处,只能缺如。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