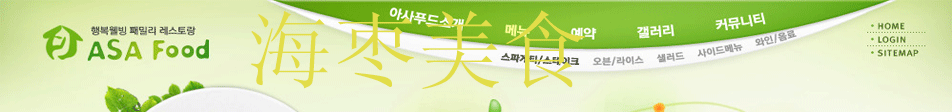|
《金瓶梅》究竟成书于何时,它的作者又是谁,这两个问题困扰了人们多年。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不仅有资料缺乏的客观原因,也有认识上的主观原因。 要想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继续挖掘有关资料固然十分必要,但对现有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综合分析,尤其是从传播角度来加以观照,或许能够有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认识。 一《金瓶梅》的早期传播是通过人际之间进行的,这些最早看到或听到《金瓶梅》的接受者所透露出的信息,是我们了解其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 明代万历二十四年(),著名文人袁宏道给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 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关《金瓶梅》流传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记载。尽管这封信篇幅不长,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 一,最迟在万历二十四年,《金瓶梅》已经在社会上开始流传。 二,当时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着,而且流传的范围极其有限,像袁宏道如此有名气的文人,都不知道其来源。 三,袁宏道虽然仅仅看了前段,但已经赞不绝口,认为要远远胜过枚乘的《七发》。 与这一记载密切相关的是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的一段话:“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1] 这里说到的董太史思白,即董其昌;中郎即袁宏道。那么,袁中道是何时见的董其昌呢?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袁中道从乃兄袁宏道在真州是万历二十六年,因此袁中道与董其昌见面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前。 与前所引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相对照,可以进一步证实,董其昌是较早拥有《金瓶梅》的少数人之一,并认为《金瓶梅》“极佳”。 董其昌只对袁中道提到了《金瓶梅》,但并没有拿给他看。袁中道后来在真州才从其兄袁宏道处看到了“全书之半”。 言外之意,经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袁宏道仍然未能拥有全书。 以后袁宏道又多次提到《金瓶梅》,如在给谢肇浙的信中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蒲桃社光景,便已八年……”[1] 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及友人江盈科、潘士藻、谢肇浙等在京结蒲桃社是万历二十七年的事,八年后应是万历三十四年()。 袁宏道称“久不见还”,看来所借时间非止数日。但这时袁宏道似乎仍然只有全书的一部分,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说道:“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1] 从年到年,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袁宏道依然未能得到全书,这不仅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而且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尽管如此,袁宏道仍然对《金瓶梅》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觞政·十之掌故》中说:“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 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1]显然已将《金瓶梅》与许多著名作家作品相提并论了。 还有两条资料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所说:“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1] 王宇泰即王肯堂,王百谷即王稚登。据刘辉先生考证,屠本畯见到王肯堂的抄本约在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一年(—),若此说能够成立,则比袁宏道见到《金瓶梅》的时间还要早三、四年。但屠本畯同样“不得睹其全”,只是说“书帙与《水浒传》相埒”,又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二是薛冈在《天爵堂笔余》中所说:“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鄙斋,予得尽览。”有研究者指出,薛冈见刻本的时间大约在万历四十七年(),那么他见文吉士抄本应在万历二十七年(),该抄本也是一不全抄本。 种种迹象使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金瓶梅》还未全部写完时,已经开始在有限的人群中如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刘承禧、王稚登、王肯堂、屠本畯、丘志充、谢肇浙、沈德符文吉士、薛冈等人中流传开了。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话也常被人们所引用。这段话说,袁宏道《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但自己“恨未得见”。 万历三十四年(),在京城里遇见了袁宏道,他问袁宏道是否有全书,袁宏道回答说“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过了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进京参加考试,“已携有其书”,他便借来抄写了一部并带回了家乡。这段话与谢肇浙《金瓶梅跋》所说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细微区别,按照沈德符的说法,万历三十四年时,袁宏道不仅没有《金瓶梅》全书,甚至也没有读过全书,但他知道刘承禧家有全书。再一个重要信息是,到了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也有全书了。沈德符又接着说,他将此书带回家乡后,他的朋友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商出重价购刻。 另一友人马仲良“时榷吴关”,也劝他满足书商的要求。但沈德符认为,这类书必定会有人刊刻,一旦刊刻后,就会“坏人心术”,因此他将此书“固箧之”。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从一般情理上看,这部“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应是最早的刻本。 问题在于,沈德符所说的“未几时”究竟是什么时间。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万历庚戌(),吴中始有刻本”,就是根据了沈德符的这段话,并且将“未几时”定为一年。 但据李时人先生考证,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至万历四十二年(—),因此,这一刻本只能出现在该年之后。 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言,该序言写于万历丁巳年(),与万历四十二年仅仅相隔三年,因而有理由认为,这一丁巳年的刻本即使不是初刻本,也是与初刻本相距时间不长的一个刻本。 二 沈德符的上述记载对我们了解《金瓶梅》抄本、刻本的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他的另一段话又使人们对《金瓶梅》的成书时间陷入了迷雾之中。他说:“闻此(指《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根据这段话,在很长一段见内,人们认为《金瓶梅》应成书于嘉靖年间。直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动摇。实际上明清两代的许多人都主张“成书于嘉靖说”,除了沈德符外,前面提到的屠本畯、谢肇浙以及众多清人都持此说。 近代学者蒋瑞藻、现代学者冯沅君、龙传仕、徐朔方、朱星、周钧韬、刘辉、陈诏、卜键等依然坚持此说。 其主要论据一是明人笔记的记载不应轻易推翻;二是书中的许多内证如佛道二教的活动,海盐腔及[山坡羊]等小令的流行,太监、皇庄、女番子、金华酒、书帕等均为嘉靖朝事。 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2]一书根据小说中写的都是嘉靖时事,其中的戏曲演出无万历剧目、声腔无昆曲,从而判断该书“写作在嘉靖末年并基本完成于这一时期”。 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一部明万历丁巳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很快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第二年郑振铎先生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把《金瓶梅词话》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3] 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通过对明代一些典章器物的考证,进一步认为“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中。”[4] 年美国汉学家马泰来先生在《麻城刘家与〈金瓶梅〉》一文中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一年之前,[5]年鲁歌、马征先生在《〈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一文中认为在万历十九至二十五年之间,[6]香港学者梅节先生年在《〈金瓶梅〉成书的上限》一文中认为在万历五年至万历十年之间。[7] 年许建平《“金学”考论》一书从七个方面论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六年至万历十一年之间。[8] 黄霖先生的考证更为具体,年他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就《金瓶梅词话》抄万历十七年前后刻印的《忠义水浒传》的事实说明:“《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 第二年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通过考察小说的干支年月和人物生肖,认为作者可能就是在万历二十年动手创作的。 两年后又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文中提出了五条证据,其中关于“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流行于万历年间,以及《别头巾文》见于万历年间编成的《开卷一笑》两条更有说服力。[9] 还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成书在嘉靖与万历之间。年张鸿勋在《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题材》一文中认为嘉靖说与万历说“没有多大的出入,既然确切的年代无法知道,那么它大约的年代就在16世纪上叶,再具体地说,是在嘉靖与万历之间。”[10] 年杜维沫的《谈谈〈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及其他》[11]等也从不同角度重申了这一观点。 年潘承玉《〈金瓶梅〉新证》一书认为,《金瓶梅》一书所写的时代,是佛教由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由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因而,小说反映的不仅是嘉靖朝的历史或万历朝的历史,而是从嘉靖中期至万历前期这一时间跨度大得多的历史,小说最后定稿于万历十七年以后。[12] 上述种种观点之所以各执一词,关键在于对“成书”一词的理解不够一致。“成书”者,书已完成之谓也。 而这一完成过程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某一天忽然一部完完整整的《金瓶梅》摆在了人们面前。那么,何时可以算作书已完成?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一是以小说只写出了一部分但已在社会上流传为准?还是以小说全部完成并有正式文本流传为准?二是假如小说已经完成,但作者或拥有者没有公之于世,而在若干年后拿出一部小说并宣称这是很早以前就完成的一部小说,那么谁来证明这一点呢? 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认识,争来争去自然没有结果。按照一般的理解,只有作品全部完成并已在社会上公开传播,才可以说该小说已经成书。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这一原则,那么《金瓶梅》的成书时间问题也就可以有一结论了。 事实是,在万历丁巳刻本之前,尽管很多人都提到了此书,但真正见到全书的只有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所说,万历三十七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但仍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这时距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刻本不过八年。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袁宏道只是读了数卷,虽然他说到“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但时间不会太久,否则他肯定要设法借来抄阅。 再按之沈德符非常肯定的说法,“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依据当时的刻印技术水平,一部百万字的著作从雕版到印刷,也非短时间所能办到。 因此有理由认为,全书的完成就在万历三十四年()前后。而此前种种关于《金瓶梅》的信息,只能说明《金瓶梅》正处于尚不成熟的创作过程之中。 三 最早提及《金瓶梅》作者的仍然是袁中道、屠本畯、谢肇浙、沈德符等人。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 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藉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谢肇浙在为《金瓶梅》作的跋语中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1]不难看出,这些最早读过《金瓶梅》的文人对该书作者却都十分茫然,且说法极不一致。 其内中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确实不知道作者为谁;二,知道作者为某某,但出于微妙原因而不便说明。 但假如是后者,又会让人感到不解,莫非几个人都已经事先商定好,从而取得了口径的一致,都来为作者保密? 再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确实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作者的名气也就不会太大,换句话说,不太可能是所谓的“大名士”。 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言,开头便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这便是作者为“兰陵笑笑生”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刻本之前,并没有人提到过“兰陵笑笑生”。 这位“笑笑生”是刻书者随意杜撰出来的呢?抑或确有所指?假如是后者,所指又是何意呢?有意思的是,尽管该刻本提出了“兰陵笑笑生”,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更多的人却津津乐道于作者为著名文人王世贞,康熙十二年()宋起凤在其《稗说》中便明确此说,康熙乙亥()谢颐在《第一奇书序》中又说道:“《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1] 清代评点家张竹坡及清人的许多笔记如《寒花庵随笔》、《秋水轩笔记》又提出所谓“苦孝说”,认为《金瓶梅》是王世贞为报父仇而作。 实际上持王世贞说的这些人们是根据了屠本畯和沈德符的含糊其词引伸而来,并没有可靠的资料予以证实。 这就是说,明清两代对《金瓶梅》的作者始终没有搞清,对所谓“兰陵笑笑生”也未给予特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