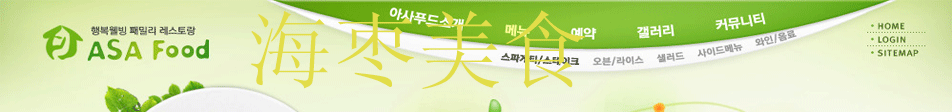|
临沂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5837446.html 喜欢我们,可“设为星标”哦~ 点击上方“岁月无敌问张欣”→点击右上角“...”→点选“设为星标★” (▲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说点过去的事 文 魏心宏 /10/ 前面提到出版社工作三宝:剪刀浆糊红墨水。老谢是使用红墨水最多用的最好的人。 那么剪刀浆糊呢,这就又让我想起一些事来。九十年代以前,作家写稿子都是用稿纸,分格和格两种,由于出版社与印刷厂关系近,所以,出版社的稿纸都特别好。那时候我们也都会向准备为出版社写稿子的作家提供稿纸。 贾平凹就特别喜欢我们的稿纸。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他寄一大包去。平凹跟我说,他要是一天不写点什么就像是白过了一样。这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平凹写作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喜欢把稿纸反过来,利用稿纸上印有的格子和行距在稿纸的背面写。我问他这是为啥。平凹说,这样多自由啊。平凹都字那时候就写得好,架不住每天写,久而久之,字就越写越有味道了。 几十年后,我去西安,满大街都是平凹题写的店名。平凹的书房里,也都是文房四宝加古董。就跟康熙皇帝的三希堂差不多。听人说平凹现在的字可值钱。我就跟他要了字。平凹当然不会要我的钱。 (▲ 字:贾平凹)后来这件事也被很多作家都学去了,一个个都在家练字。拉屎攥拳头,暗地里使劲。陈忠实后来也写字了。也给我题写了一幅。老陈说,写什么你说。我就一想,白鹿之原吧。于是,老陈就给我写了。老陈也是我们社稿纸的爱好者。我也给他寄。出版社那时候的制度是,买稿纸的钱要在稿费里扣。我想想太小儿科,就说我自己用的,领导也没注意,我就钻了空子。 (▲ 字:陈忠实) /11/ 我把老陈平凹送我的字找出来了。晒一下。还有刘醒龙给我的字。其实,给我题过字的人很多,一时找不出来了。 (▲ 字:刘醒龙) 我与老陈平凹认识很早了。七十年代末期,陕西举行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我去了。 (▲ 作家:柳青) (▲ 作家:杜鹏程) (▲ 作家:魏钢焰) (▲ 作家:王汶石) 我本意是想去拜访几位陕西如雷灌耳的大作家的。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李若冰、胡采、贺抒玉的,后来也都见到了,却在会上见到了陈忠实和贾平凹。 (▲ 作家:陈忠实) 老陈当时还在西安灞桥一个人民公社当领导,四十多岁。却已经是满脸皱褶,一开口就是浓重的陕西腔。老陈人很厚道,或许也不认识几个像我这样的上海人,就对我格外好。这种友谊保持了几十年。直到老陈去世。我对老陈最抱歉的就是没有促成他活着的时候写一部回忆录或者自传。我曾向他提出过。老陈说,让我想想。后来老陈为我写了一部创作谈的书稿《寻找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句子》,而我想象和期待中的自传却未能写成。老陈去世来得突然,让我除了痛心外感到无比后悔。 平凹那时候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印象中他抽烟很凶。跟我说,每天出门,四个口袋都要装上烟,否则不敢出门。平凹请我吃了第一顿羊肉泡馍,饭碗就像一个脸盆,吃得我汗流浃背,好不狼狈。平凹的妻子小韩以前是唱秦腔戏的,很传统。西安作家孙见喜写了《贾平凹其人其事》,写了平凹和第一个女友在西安鼓楼大街手拉手,小韩读了受不了了。我说孙见喜,瞎写啥呀!可见小韩是多么保守。 平凹的个大度乐呵的人,脾气好,说话也慢悠悠,不爱激动。他的最大本事就是把写作坚持了几十年。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都集体转向去读外国作家的书,平凹也不掺合,就写自己的作品。他对学人家外国人的路子写中国小说这件事不感兴趣。八五年后,他写出了他的扛鼎之作《废都》,那时候我不在上海,就给他拍了电报,伟大之作。就四个字。 (▲ 作家:贾平凹)/12/ 八十年代初,编辑部里来了欧琳。欧琳姓卢,父亲卢于道,我国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泰斗,美国芝加哥大学解剖学博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授。欧琳是我国电影学院第一批毕业生,欧琳年轻时候长得漂亮,在电影学院有校花之称。毕业后被分配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可那时候的欧琳,脑袋里充满着理想,坚决要求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结果去了新疆。在那里深入生活,与新疆的游牧民打成一片,写出了电影《天山上的红花》,由大导演崔巍执导,结果一炮走红,阿娜尔罕阿依古丽瞬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欧琳在新疆结了婚,生了漂亮的女儿。之后便与丈夫离婚。离婚后依然觉得不行,又与丈夫复婚,生下了小不点儿子。儿子出生后又再次离婚。这个时候,卢于道年事已高,为了照顾老教授,国家出面将欧琳调回上海。欧琳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已经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当年的激情不在了。父亲对欧琳这样反复与同一个人结婚离婚很有意见,加上欧琳的弟弟也已经是复旦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了,所以对于女儿的归来,父亲并不特别高兴。好在欧琳的妈妈还在,心疼自己的女儿,经常把她叫回家去,一家人聚聚。欧琳回到上海后自然还会寻找丈夫,又与一位美国回来的老王认识了。老王的前妻病故,虽说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但老王却对前妻一往情深,专门在家留了一间前妻居住过的房间,布置一如妻子活着的时候一样。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老王是在传统生活中几乎活了一辈子的人,见到了犹如喀秋莎一般美丽的欧琳,自然就很上心。而欧琳其实是一个想找颗大树停下来歇歇脚过太平日子的人。两个人在错觉中相爱了。结婚后自然就不那么顺畅了。老王的矛盾在于,既想过浪漫的生活,又要妻子能像旧时代的女性一样,鞍前马后地照顾他。欧琳的角色确实难当。她非常不开心。有的时候也会与我谈起这些话题。我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傻乎乎的毛头小伙,根本不懂得这些。 欧琳在编辑部里呆了十多年,身心已经很不好了,一过了两千年,她就去世了。我去了她的追悼会,见到了依然美貌的欧琳的女儿,长大成人的儿子,以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老王。从老王的表情看,他确实爱着欧琳。只是他们不是一路人,不该走到一起罢了。 /13/ 出版社里有两位诗人,宫玺,姜金城。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也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从年纪上说,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但是他们从不把我当成晚辈,小魏小魏的叫着我,不分彼此。两位大诗人性格思维与众不同。出版社领导就把他们二人安排在一间办公室里,其他的人尽量不要去搅和他们的事。诗人都是爱激动的。他们经常两个人在一间办公室里讨论一件事,比如刚读过的一首诗。两个人都非常激动。高音大嗓。外面的人还以为在吵架。其实,他们各激动各的。没事。 诗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正直天真。他们对出版社的会议或者什么新规,一概不知,也不关心。他们宁肯去关心鸟是怎么飞翔的也不关心什么房子分配评定职称之类的事情。 (▲ 诗人:宫玺) 宫玺是老资格的诗人,当年也是空军当中与阎肃齐名的诗人。八五新潮后,他的思想受到了洗礼,诗风也为之大变,经常会有一些“夜空,你不再明亮”之类包藏深刻寓意的句子往外蹦。宫玺对自己的进步非常看重,与阎肃老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和春晚博得巨大名声写什么“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之类的雕虫小曲压根儿看不上眼,还是觉得自己那种肃然起敬的探索新诗更有意思。无怨无悔地坚持。 (▲ 诗人:姜金城) 姜金城则要随和一些。老姜写诗也挺怪,有的时候是先写下句,再写上句。我问老姜,这是为了韵脚?老姜说,我想到了好句子就要先写下来。两位老诗人为出版社编辑了一套新诗丛。舒婷的成名作《双桅船》就在其中。很多年后,我让舒婷谈谈对两位可爱诗人的看法,舒婷说,他们都是好人。我与两位大诗人的友谊至今都没变。宫玺现在听说已经足不出户了,腿脚不便。我想去看他。可他坚决不让。老姜时常还跟我通通电话,问候一下。老姜的爱人孩子也都跟我很熟,孩子们都叫我“小魏叔叔”。 /14/老谢最终还是没能抗得过去疾病对他的威胁。 年3月31日,上海部分曾经受到过老谢帮助过的作者举行了一次专门感谢老谢的座谈会,会议的名称就叫《谢谢老谢!》,在这个会上,一些作家都把自己在写作之初如何受到老谢的帮助、如何看到老谢大笔一挥,修改稿件对自己写作犹如醍醐灌顶般的触动,来了一次畅谈。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一路经历,每个人成熟的过程也都不一样,一样的只是他们在走向成熟和成功的道路上,都曾得到过老谢慷慨无私的帮助,这种帮助或许就是几个病句或者表达模糊的提点,或许就是几个标点的错用,但是,都被老谢看到并给予了纠正。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们怀着对老谢的感恩之心来讲述自己的心情。 老谢自然也很激动。文革以后,人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变,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表里不一,以邻为壑,种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比比皆是。而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老谢的这种为人之风不啻是一缕清风,一种对不良风气的批驳和反击。作家们以个人的体会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谢谢老谢,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对社会对人性的呼唤和赞誉。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也就是在这个会上,老谢或许受到了内心深处极大的触动和感动,情绪已经临界危局。多年来对自己已经略为超重的身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脑袋一歪,身体就此倒下。等到医院时,医生已经宣布,老谢由于脑溢血陷于极度危险之中。医院施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能挽救过来,老谢最终离开了人世。作家们都对此抱以极大的遗憾和痛心。老谢去世时只有73岁。如果早一点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防治和措施,老谢绝不至于在这个年纪就此止步。 很多年后,作家们再次在静安宾馆顶楼聚会,回顾老谢的一生,对他的去世深表难过。我记得诗人田永昌还当场朗诵了一首他的诗,诗名叫做《老谢,你依然活着》,充满温情的回忆与诗人才有的激越情感让所有的人都落泪。 /15/九十年代初,我去四川出差。克非那时候已经回到绵阳了。老作家突然发现,我国的所谓红学研究存在大量谬误。以克非的博学态度和顽强个性,他是说什么也不会默不作声的。他停下笔来,一鼓作气将所有与红学有关的书籍全部搜齐,开始做起了系统的研究。我只要一去他家,他就会滔滔不绝地和我说他的新发现。克非的最终结论是,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红学。所谓红学也根本没有触及《红楼梦》研究的核心问题。克非就此写出了好几部专著。我被他的热情和激辩所感染。最终,我们社为他出版了他诸多研究专著中的一部。 (▲ 作家:克非)当我再次去往四川见克非时,他正在准备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会前所有的代表都集中在成都的金牛宾馆。我去了金牛宾馆。克非那一次和我一起在院子里走走,克非显得非常沉默。这个情形很反常。问过后才知,原来是小女儿因为脑部长了个瘤子而去世了。说到这个女儿,克非老泪纵横,因为女儿自己找了一个在父母看来根本不合适的人恋爱,克非为此大怒,女儿要么放弃,要么就不要回来了。倔强的女儿竟然离家而去,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克非说到这一点,就特别难过,泪流满面。我认识克非很多年,第一次见到他那么难过和痛苦。我也非常难过。小女儿去世后,克非身边就只留下了大女儿。二女儿脚印也和北京的诗人多多恋爱去了北京。等我再去青义镇看克非的时候,我觉得那里已经冷清多了。 /16/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最惦记的就是处在地震核心区的克非。我几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克非家处在绵阳市的西部,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那里已经与绵阳市区连成一片,过去那个孤立独处的青义镇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正是这个地形,让我尤其焦虑。上游形成的堰塞湖高悬在头顶,一旦崩塌,克非家那个临河而建的小楼就会首当其冲。我劝克非还是赶紧出去躲躲。可是,克非坚决不听。他的博学性格再次发挥:我已经研究过了,那个堰塞湖根本不可能崩溃,所以我很安全。尽管克非是这样说,我的心里依然难以释怀。我每天都在看与绵阳有关与堰塞湖有关的新闻,希望能有点平安无事的消息。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结果一切都按照克非的预言而过去了。我的心里也总算是平定下来。克非啊克非,你真是太牛了! 年1月25日,克非在青义镇的家里半夜起床上厕所,结果突然倒下了。消息传来,我痛哭流涕,这么健谈这么博学、这么热情、活得这么真切的克非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我给脚印打电话,脚印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离开我们了!那句话,让我一时泪奔。人世间的真情啊,真是折磨人! /17/ 说到克非,让我还想起一些往事。七十年代末,克非、奚青、朱光亚都来了上海,住在瑞金二路的招待所改稿子。那时候,从上海近郊农场也抽掉了一批能写作的青年人一起来写作。他们当中有后来成为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孙颙、有写了《陪读夫人》的王周生。叶辛也在。他们都在招待所里,每天都来。我也是只要下班就去招待所找他们玩。 克非奚青朱光亚他们三位最爱争论。一次争论的主题是,黑人女性到底好不好看。奚青朱光亚认为,怎么说都不好看。克非不同意。他认为,觉得她们不好看只是你们的看法,黑人们未必这么着看。我有点赞同克非的看法。几位作家争论不休,谁都说服不了谁。 王周生那时候还是小姑娘,性格质朴,挺受欢迎。当时,周鲁卫正在追求王周生。周鲁卫是大作家周而复的儿子,正在复旦大学念书。不知为何,王周生就是不肯。大家都来劝她,甚至拿话激她。王周生就是不言语。有一晚,与叶辛合作写书的鲍正衷突然来宣布,王周生结婚了。鲍正衷与周鲁卫住邻居。他的话不得不信。结果,真的结婚了。据说王周生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了周鲁卫那里。周鲁卫看到她同意了。蹦起来抓到了房顶。 孙局长那时候也正是翩翩少年,相貌英俊。他的写作水平已经很高了,不要说在上海,就是拿到全国去都是最好的。他们正以自己的书写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不久后,文革后的高考到来,他们走进了大学,开始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18/开篇说到了金磊,却兜了一大圈。我还是接着说说金磊。 (▲ 作家:金磊) 上周我去了常州下辖的金坛。金坛有座茅山,一共是由三座山组成,大茅、二茅和三茅。景色非常秀美,环境保护的无话可说。距离上海这么近,竟然有这么一个天然的好世界我真没想到。金磊现在就住在茅山。一个小小的村落里,他在那里买了一所旧房子,然后自己又把房子翻建了,有个小庭院。金磊住在那里,在那里写作。我也有好些年没有见到他了。在我的印象里,他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结果一问,他是年出生,似乎也不年轻了。年,我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他。我那一年突发灵感,觉得文学就将出现一个大的变潮,我开始有意识地在一批年轻、以前未曾写过发过作品的作者当中选择出一些我认为有前途的作者,金磊就是其中之一。我把这些作者的作品全部编进了一个独立的栏目:七十年代以后。最初被我列入名单的作者当中有,卫慧、棉棉、胡昉、李凡、弥红、魏微、赵彦、赵波、周洁茹、朱文颖、金磊、马力、王齐君、陈家桥、姜宇、方子玉、赵岩艳。随着他们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引起了读者和全国许多文学刊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