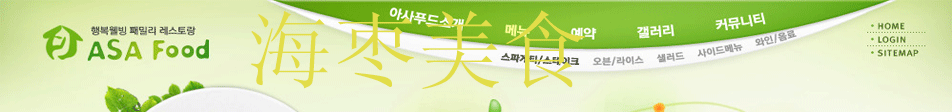|
《金坛作家》金坛区作家协会唯一官方平台 作者 睢爱春 烤山芋 环顾四周,不远处一个穿着黑大褂的老汉推着板车向我走来,银发在风中飘飞。板车上载着一个巨大的灰不溜秋的桶,顶端有一个圆形的口子,口子的四周排放着大小不同,或泛黄或泛黑熟山芋。这迷人的香气大概就是从这里弥散开来的吧。 “我也要吃一个!”妻子孩子似的欢快起来。 手里的山芋温热绵软,在尖头向四面掰开,形如盛开的花朵,金黄透紫的肉就呈现了眼前。我和妻顾不得体面,大快朵颐,每一口都甜得丝丝入扣,软得流光泄玉。 这唯美的心境让我的回忆穿梭到了几十年前的童年。 艰苦的岁月里,物质匮乏,山芋给予了穷苦的人们无尽的馈赠,可以让饿瘪的肚子吃上一饱。山芋可以做山芋丝、山芋粥,山芋粉、烤山芋……不管哪种形式,农人们总是爱不释手。 我对烤山芋是情有独钟的。 冬季来临,寒风裹挟着雪花飘落,浑身每一处都是冷飕飕的。每到傍晚,手上已经冻出冻疮的我,早早地抢着坐在灶膛口,点起稻草,舔舐的火苗映红了脸膛。母亲系起围裙,在灶台上忙碌着,锅盖的缝隙里冒着浓浓的热气,香味充盈着不大的空间。 在灶膛口,堆放的草堆里,埋着圆溜溜的山芋。母亲说,这些山芋若不放在草窝里捂着,会冻坏的。这些山芋有大有小,形状也各异,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我捧出三两个,往灶膛里噗噗地扔去。很快,它们就如石块沉到水底,躺在燃尽的草灰里,等待着成熟。 草堆旁是母亲码得整齐的柴火,是她留着年底蒸点心用的。我会悄悄地塞进几块,这样的话,火力更大,山芋熟得更快,更彻底。 吃过晚饭,大家围坐在灶门口,唠着嗑,道着家长里短,说着村里的大事小情。灶膛里的火苗渐燃渐熄,山芋的香味早已溜了出来,在屋子里弥散。 父亲说,差不多了。 我迫不及待地扒开草灰,用火钳小心翼翼地夹住山芋,把它们宝贝似的请了出来。 冒着热气的山芋浑身焦黑,残留着点点的火星。我伸手捉住一个,一缩手,烫得龇牙咧嘴,赶紧放下,也许“烫手的山芋”因此得名吧。父亲和母亲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几番尝试,终于再次攥入手掌。手上、脸上早已经黑灰一片。 不用细心去剥,稍一用力,山芋皮和金灿灿的肉就已分离。外焦里嫩,那黄得发黑,红得发紫的肉松软如泥,而最中间部分仍保持着硬朗的风骨,一口下去也别有一番滋味。 于是顾不得烫,嘴巴吸溜着,大嚼特嚼,腮边连着都胡了一片。 尤喜山芋头尖尖的部分。这里体积不大,受热最为透彻,外皮早已烤得黑如焦炭,于是肉早已和皮连成一片了。我把焦皮捧在手心,伸出舌头,准备去舔。母亲呵呵笑着拿来了调羹。于是,开创了山芋的新式吃法。一勺一勺地挖进口中,如琼浆玉液,爽入心扉。味道特别甜,感觉空气里都能拉出甜丝来。 现在,我这样的农村娃城里也买了房子,住进了钢筋水泥铸就的“鸽子窝”里。烤山芋这样的饕餮大餐,已成奢望。每每回到乡下,我总是坐到灶膛口,怅然若失。母亲也是会心地一笑,“想吃烤山芋了吧?” 当然,烤山芋并不是只我一个人喜欢,有网友看到烤山芋的图片,有感而发,即兴吟诗一首,字里行间里写满了对烤山芋的痴情。 炭火烧炸松枝油, 嘴吹手扇熏眉头。 慈父眼望炭与火, 童子含笑盼苕熟。 PersonalProfile 作者简介 睢爱春,70后,金坛区作协会员、一个热爱文学的语文老师,中学高级教师,多篇散文和小说见诸报端和媒体。“麦田文学社”的辅导老师,带领孩子们徜徉在文学的天地里,感受文字的美。 END 金坛作家
|